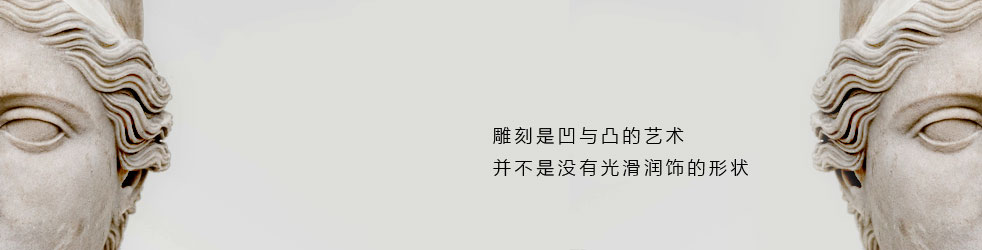
亨利·摩尔的雕塑对传统雕塑而言,他不仅讲求外形,而且对内形的塑造亦十分讲究。传统的雕塑,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是米开朗基罗、罗丹,他们的雕塑语言更多的是塑造出一个结实、完美、造型生动的外形。外部形体谁都可以看见,较容易被人理解和观察到,而走向摩尔的许多雕塑,我们透过外形还可以看到优美的内部形体和空间,而内部形体和空间却常常不被人理解和领悟。正是摩尔把我们引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使我们的目光能够真正的在三维的雕塑中遨游,就像我们去观赏一座优秀的形体美观、充满震撼力的建筑物一样,它不仅在外观是看起来能深深的打动人,我们还能走进被各种材料围合的室内空间之中去,并且这一被围合的室内空间是那么的美丽动人。前人们却从未发现在雕塑中还有如此完美的内在空间,即便是有谁曾无意间踏入过这一内部空间,他也胆颤心惊地从这一充满遐想的内部空间中逃一般地走出来。他们是那么害怕沿这一条陌生的道路走下去。然而,亨利·摩尔,这位伟大的二十世纪现代主义雕塑的代表人物,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而且他迈出的这一步是那么的大,声音那么的嘹亮,脚步声使整个雕塑界为之震动,人们惊讶的目光是那么整齐划一的从古典雕塑转向了现代雕塑的三维形体之中,人们转着角度审视摩尔的一件又一件生机勃勃的雕塑。人们的目光从那个时刻起,似乎又重新找到了一个全新的观察世界的视点。
在审视观赏亨利·摩尔的雕塑时,人们常常提及中国的太湖石。无论亨利·摩尔是否曾看到或观赏过太湖石,但我们是那么明确和肯定的知道,亨利·摩尔的雕塑从三维形体上来说,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太湖石对三维形体空间的理解和展示,亨利·摩尔的这些带有空洞的作品不仅没有破坏雕塑的形体语言,反而是增加了雕塑的深度和整体造型的美感。他似乎要把我们带到一个遥远的世外桃源中去,在那里充满了神秘和好奇,在那个空间中有着爱尔兰风笛鸣奏出的一篇篇悦耳动听的音乐。亨利·摩尔自己也曾说:“多年以来,我都希望作品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应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将实体作为虚空的框架,便出现雕塑中虚空的实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强调出作品的内外空间的延续性,给造型带来雕塑的新概念,发掘雕塑形式上可充分表现的潜在可能性。 亨利·摩尔在他的雕塑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两大主题,“母与子”和“斜卧的人体”。在他的“母与子”之中更多地展现出的是一种对人类固有情感的强烈体现,展现出的更多的是庄严、宁静和温馨,一心一意的呵护着爱,一种深深的幸福家庭之爱,在他的这些作品之中对形体空间的展现还是那样的保守,我们依然能从中读到传统雕塑对三维形体的一种固有的展示。那样的大胆和豪放,《母与子》这样主题的传统观念或多或少对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一到了《斜卧的人》这样的主题中,他就变得是那样的无拘无束,设法摆脱在三维形体上他总是能够在外形和内形上都大刀阔斧的雕琢;而一到十分讲究的细节上,他又是那样的精微缜密、他总是那样小心翼翼的精雕细刻,将形体空间语言展现到极至,力求使形体空间的虚与实、动与静达到尽可能的完美。 亨利·摩尔对这种内外形的探索和研究是那样的持之以恒。从1929年到1930年,他创作了第一批独特的斜卧人体,到1961年至1963年是最后的斜卧的人体,令人惊讶的是其形态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姑且不论对同一母体的坚持,惟一明确的是差异也只是表面的,而不是体积,只是音调,而不是节奏。这意味着独特的雕塑价值——体量和表面张力的价值——贯穿着这位艺术家一生的创作发展,而所变化的只是覆盖着硬骨和肉的皮上的皱纹。试把1931年创作的坎伯兰雪花石膏雕塑《结构》,同1960年到1961年创作的《斜卧的人体》铜像比较一下,甚至把1929年至1930年创作的斜卧的人体,同1961年到1963年创作的不朽的三件组合成的人像比较,他们所采用的材料比例和技巧手法越是不同,它们就越显得具是同一事物、统一形态或格式。在这位艺术家三十余年成熟创作期内也存在着发展。这种发展或许可以叫做原形意识的发展,尽管存在着某种短暂的偏差,但贯穿这位艺术家整个生活的一直是一种深深的超自然感——对事物所体现出的超自然力量感,或一种泛灵活力充满所有的自然形体。他是那样执着地在他的一生中探索这种内外形体的互动和变化,就像八卦中的阴阳互动一样,在他的内外形体之中的这种互换是那样神秘,又是那样充满诱惑,总是自然不自然地将我们的视线强烈地吸引过去,他将我们带入作品本身。同样,又将我们带到无限之远的自然中去。但是,这并不是情感偏爱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形体偏爱的问题,而仅令是这样变化莫测的三维内外形体是如此地让亨利·摩尔着谜。使他在其一生中不断探索前行,早已忘记了他返程的道路,且从无回头之意。 海德戈尔曾指出:“真就是艺术,艺术家把存在带到世界上来,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世界。”以亨利·摩尔为典型代表的西方现代雕塑,就是要去揭示这个真实存在的内部空间,雕塑为什么不可以去揭示内部空间的形体美呢?人类总是在不断禁锢自己的思维,同样又总是在不断地解放自己。罗丹推开了二十世纪雕塑的大门,把雕塑引向了现代。杜尚又将小便池倒置在美术馆,并给它命上了一个动听的名字《喷泉》,将人类对雕塑的重新思想和审视。如果我们继续称所有的独立的三维空间的造型艺术作品为“雕塑”的话,我们在亨利·摩尔的雕塑作品中已经看到一种全新的三维空间的艺术作品。这样的作品,既不是传统意义上“雕刻”出来的,也不是浇铸翻制出来的,更准确地说是建立起来的,如同建筑物一样,在形体空间上以一种内外形结合的方式构建出来的。亨利·摩尔似乎在这些《斜卧的人体》中忘记了大师(罗丹)的忠告 “以深度造型 清楚地表明主要的面 设想形体直接把向你;所有生命从中心点汹涌而来,由内外向外的扩张。”可他又是那样的忠诚于先辈大师们,在他的三维空间之中,无论每一个面每一个视点都以更加张扬的方式表态和述说着三维深度造型的原则,但他又是那样的不满足先辈以一点为中心的视觉观察的方式来造型,在他的《斜卧的人体》中,我们可以不断地更换视觉观察点。我们发现随着观察点的变化,我们眼前的景象就为之而变,大有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移步换景的意味。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体,表达出不同的形体情感,而这些角度和形体完全的贯穿起来便成为他这一伟大作品的全部含义。 进一步说,亨利·摩尔与续集雕塑相比较,他们的差异就在于一个墨守韦尔夫林称作的“开放的形体”置于大自然风光之中,他十分强调女性人体与自然风光之间的相似之处,即使在繁华都市为背景的定制作品中也仍然如此。1962年,当亨利·摩尔谈到风景对他的影响时,他说:“将人像与风景交织在一起,这正是我在雕塑中试图要作到的,这暗示了人类与大地山峰以及自然风光的内在联系。如果用诗意的语言来指出,那么山峦的起伏正像羚羊那轻快的一跃,而雕塑本身就像诗一样充满隐喻。”这种开放式的形体、风景般格调的雕塑,在亨利·摩尔的作品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尤其是在他一生的后几十年为世界各地户外公共环境制作的大型雕塑中,这一点体现的格外明显。亨利·摩尔的这些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雕塑,他所创造的这引起内外形体空间,常常打破人为时间的限定,他不仅可以在北海公园这一东方古老的皇家园林中的自然环境相完美的结合,且丝毫没有时间上的隔阂。在这一点上,他的雕塑在时空上又大大地突破了太湖石所局限的东方人文环境为背景的雕塑作品。太湖石不可能与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人文环境相密切的结合,太湖石的形体空间美只能拘泥于东方文化为背景的古典自然环境之中。这种对于时空环境的超越,不是每个古典抑或现代的雕塑能够达到的境界,斐底亚斯、米开朗基罗、罗丹都没有达到,可在亨利·摩尔的十指之间,这种时间的隔阂完完全全的在他眼前消失殆尽。 与自然环境与空间的完美结合所形成的美,自然这种美不再是孤立的美,这种美对人类心灵所产生的震撼感同赖特的“流水别墅”一样,充满了宁静与和谐,走入亨利·摩尔的雕塑空间与走进“流水别墅”所营造出的自然空间环境所达到的境界是那样的相似。赖特,作为一个同样深谙中国古典哲学的西方二十世纪的建筑大师,在他的“流水别墅”中同亨利·摩尔的雕塑一样,他将建筑空间与自然空间完美的结合。真正做到了艺术为天、环境为地、天地合一、以人为本,把人与自然完美的结合在他所营造的室内外空间环境之中。在这里,森林、小溪、岩石和所有的结构要素都如此安静地结合在一起,尽管溪流的音乐还在响着,便你听不到任何的噪音,你倾听着流水别墅的声音就是在倾听着乡村的宁静与祥和。这是“天人合一”的典范这美,这完全是天籁的音乐。亨利·摩尔这个与赖特同属二十世纪的雕塑大师,他与赖特似乎同时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同样利用各自的双手,运用不同的形式语言门柱了同样的哲学、美学法则——将空间由内而外,由外而内向环境延伸,不再仅仅把目光停留在物体的外部轮廓,而是与环境相互沟通,营造一种新的人文环境而且毫无雕饰之感。他不仅让外形得以张扬,甚至向空间和环境之中扩张和延伸。摩尔对雕塑在空间的这种永不停息、坚持不懈地探索,使雕塑在空间是带来的发现是无止境的,摩尔的这种对雕塑空间的探索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内涵与我国的传统人文精神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人每当提起摩尔的雕塑就要提及太湖石的原因。 老子曰:“钟不空则哑,耳不空则聋,居不空则无以居。”庄子曰:“七窍具而混沌之。”这都是东方的“无”的观念的。“无”的观念即“窍”、“孔”、“洞”的观念,也既是太湖石所显现出来的虚空间所蕴涵着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中国自古以来受这种虚实——阴阳转换的哲学精神的熏陶,也便自然地形成了欣赏抽象艺术的审美观。在西方探索艺术的精神时,中国国画早以明确指出,艺术作品不仅仅是超写实的再现,更多的应该是作者内在的精神品质的体现。在雕塑中,我们自然就会钟情于自然景观中的卧佛山、望夫石、太湖石这一类的自然抽象雕塑了。摩尔的雕塑步入中国,身受中国人所喜爱也不足为奇了。因为在这里,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摩尔的雕塑所阐释的精神内涵与我们的传统人文精神是那样的高度一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情感的共鸣是那样的自然而毫不做作了。东西方文化在他的雕塑中相互交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没有一丝文化相互碰撞的痕迹,真可谓水乳交融,这和他的雕塑一样是那么的完美,今人叹服。 最终我们要不要去探讨摩尔是否研究过东方文化,已经没有太多的实际价值和意义了。我们只需深情地走向摩尔的雕塑空间中去,毫不犹豫、毫不遮遮掩掩我们自己的目光,自由自在地在摩尔的雕塑空间中翱翔。
发表评论
请登录